impala雪佛蘭1967,雪佛蘭impala黑斑羚
但相信絕大多數朋友都會把最早的硬核公路片標記給1969年的《逍遙騎士》。至少肯定是1957年以后的影片,因為那一年公路片的綱領性文本杰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問世了。
在公路片大行其道的時代,連斯皮爾伯格也趕趟兒拍過,1974年的《橫沖直撞大逃亡 》。
雪佛蘭·Impala,中文譯名為“黑斑羚”;是雪佛蘭旗下的一款經典車系品牌。目前在售款與國內的“別克·君越”共享底盤平臺,定位于邁銳寶之上,在美國的定價比君越略低數千美元,跟競爭對手福特金牛座、道奇Charger一樣屬于平價。
那是根據一宗真實新聞改編的,講的是一名囚犯的妻子因不滿社會福利機構把孩子強行送人收養,協助丈夫逃獄,過程中還挾持一名警察,一起開車去找孩子。別看狗血,當年也獲得了戛納金棕綠獎的提名,并且拿到了最佳編劇獎。
而更為大家熟知的公路片單,則是要從畫質更容易下咽的80年代算起。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無論是80年代、90年代、還是21世紀之后的公路片,不少經典之作,都是回到1950~1970美國戰后黃金時代挖掘題材。
比如《綠皮書》,就是1960年代的故事。
而攝于1994年的變態公路愛情故事《天生殺人狂》,是取材自1958年的真實案件。載著他們邊走邊殺人的車,是1970款道奇Challenger R/T Convertible,還是限量963輛的少見車型。
再比如1993年的催淚神片《完美的世界》,是從60年代的德州新聞扒墳:一名逃犯綁架了一名小男孩跑路,路上兩人產生了父子般的感情,逃犯被愛感召,結果卻被警察擊斃。逃亡用車非常豐富:
1959版雪佛蘭Bel Air
1964版Oldsmobile Vista Cruiser
而即便故事設定在當代,仍舊有不少電影會選擇那個年代的車型來承載旅程:
比如1988年的《雨人》,湯姆·克魯斯和達斯汀·霍夫曼的公路兄弟情,是在1949款的別克Roadmaster convertible里培養的:
而1990年大衛·林奇的《我心狂野》中,載著男女主角私奔的是1965款的福特雷鳥:
男主角是當年還不會亂接戲的尼古拉斯·凱奇:)
這款車很受歡迎。到了1991年的《末路狂花》,同樣是這個車,載著雙女主奔向自由,不過是1966款的:
1996年昆汀的《殺出個黎明》的逃亡用車,是1968款的Mercury Cougar:
雪佛蘭impala黑斑羚,2006年的《陽光小美女》的家庭追夢車,則是在1960年代象征著嬉皮文化的大眾T2,不過影片中是1979年版的:
而2009年的《瘋狂的心》設定是在1987年,導演則pick了1978年版雪佛蘭Suburban:
為什么公路片會存在這樣的偏愛,其實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
一定程度上肯定有美學考慮。當時的汽車設計,受到太空競備的影響,反映出非常邪魅狂狷的想象力,不必過多地遷就風阻和流線,被削弱的速度會由大發動機補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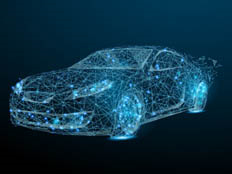
對高性能的追求,并非是豪車專屬,而是真正的平民狂歡。那時候的大發動機,馬力值甚至更甚如今的法拉利。如果你愛汽車愛到瘋狂,那是最適合穿越回去的時代。
同時,也因為那是汽車業重塑社會的高光時刻。
1950年代末,美國每六個工作人口里就有一個是在汽車產業鏈上的從業者。
年代初,全美注冊的汽車數為2500萬輛;到1958年,已經達到6700萬輛,翻番不止。汽車很便宜,平均一輛汽車的售價是在2200美元;汽油更像是不要錢,一加侖才30美分。
門檻低,滋生了在路上的樂趣,它不必要非得是由A到B的交通工具,重點不在目的地,而在旅程。人的日常本身,就是一部紀實公路片。
雖然1955年有了州際公路,但仍舊有未知的土地有待丈量,人們不知道路的盡頭是什么。探索與自由正是時代內核,汽車便是其中的連結。
由50年代的汽車數量爆炸帶來的產業結構、生活方式的變化,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美國人。

汽車是他們代代相傳的精神符號,我們經常在老片子里看到美國青少年成人禮的儀式感,就是獲得一輛車,意味著從媽寶獨立成人,準備好去探索世界的邊界了。
這些象征根植于汽車對于社會發展塑形的參與。
扯開說一句,為什么中國沒有成功的公路片?也是基于同一個原因。
但考慮到我們的基數車型,是家轎,在一個全民奔小康的年代,城市通勤功能性極強。你往往還來不及思考感悟,就已經到達目的地了。在大多數人的常識里,汽車不是一個可以完成人物弧光的空間。
但就是讓人覺得不真實。不真實的點,或許正是在于這樣的情懷內核難以和我們對汽車對公路的認知產生共鳴。最后反而還是養老和死亡問題讓我淚流滿面。
中國人尋找意義的方式,從來不是在路上。
我立一個flag,這也是以后我們難有好的公路片的原因。汽車這樣的交通工具,現在已經很難再去參與社會重塑變革,也就很難形成具備群眾基礎的深層次的公共認知或情感。或許自動駕駛之后會有其他轉機,但那更是涉及AI的新課題。
現在主流汽車消費人群,80、90后們,他們的世界邊界很少是被汽車開拓的。關鍵詞變了,與其說是在路上,不如說是在家里,或者在網上。
21世紀以后,美式公路片的存在感也很低迷,大概也和受眾變化相關。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過去20年,美國司機行車公里數下降了9%。
而年輕一代對于駕駛的熱情更是大幅下降。在2014年,16歲持駕照者的比例在24.5%,比1983年的46.2%下降了將近一半;而19歲持駕照者的比例,2014年為69%,也是大大低于1983年的87.3%。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要歸咎于大環境糟糕。如果汽車售價低于收入的10%,年輕人就會回心轉意。
但另一種解釋更能解釋自80年代以來的穩步下滑。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滲透之后,年輕人在出行、社交上有了更多的選擇,比如Uber,或者公共交通,和朋友聯系也不必非要線下見面。
時代被重塑,而汽車不是主角。
那車是1967款雪佛蘭Impala,本來想給張圖,但是找不到,只找到這張,也差不多,這是雪佛蘭Impala Super Sport,也就是Impala的超級運動版,所以是雙門的,電視劇里面的是普通版,四門的。
想一想近年成功的公路片,以真實人物傳記類為強,比如《摩托車日記》和《綠皮書》。
前者很難排除世界對切·格瓦拉這樣的革命者的崇拜;而后者,如果不是其中對平權的政治正確剛好符合近年奧斯卡日益增長的從心策略,在公路片中并不是特別出彩。
我們也能從汽車文化的角度來想想。
買不到,停產了。Impala正式停產。雪佛蘭Impala最早于1958年推出,車型歷史已有62年,至今已發展10代車型。雪佛蘭Impala的停產將為未來純電動悍馬的投產讓路。隨著汽車市場需求的變化,消費者對于轎車的需求量日漸下降,導致像Impa。
如果公路片還有一點意義,那便是對現實的反抗,對社會順從的反抗。
雪佛蘭impala 還沒有引進中國,暫時沒有賣的~67款更是沒有~
可爾今,佛系當道,還反個什么抗呢。
版權聲明:本站文章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